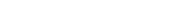科技创新70年·青稞力量
连续观测5天、每天观测4小时,前不久刚从西班牙内华达山回到南京的施勇,正在用世界最先进的毫米波单镜,观测来自黑洞周围物质的电磁辐射。但遗憾的是,由于赶上了大风天,这次观测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在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施勇看来,搞天文观测,就像农民种地,“是靠天吃饭,收成不好是常有的事”。
只不过,施勇的“种地环境”有些艰苦。很多天文台建在山上,他必须练就强健体魄,以克服高原反应。只有这样,他才能竞争到望远镜观测时间,捕捉到星系形成与演化的蛛丝马迹。
作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施勇曾首次证实低金属丰度气体极难形成恒星、首次在极端贫金属星系中探测到一氧化碳气体,还曾提出有关恒星形成的新定律。
读初中时便想当天文学家
“人类考古学家想通过研究,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也想知道,宇宙第一代天体是怎么形成的、太阳的祖先长什么样子。”一说起天文,施勇的神情就像个孩子。
自读初中起,施勇便开始对各种物理现象感兴趣。上高中时,他把老家书店里的各种物理竞赛书都淘了个遍,并在全省物理奥赛竞赛中斩获一等奖。
那时的他,每晚喜欢仰望星空,看到北极星和猎户座,便会莫名兴奋。“如果未来能做个天文学家就好了。”高三毕业后,他被保送至北京大学天文系。
2013年,结束国外博士后研究工作后,施勇回国入职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宇宙中的恒星形成问题,是现代天文学重要的前沿领域之一。此前,已有结论表明,在宇宙早期,第一代恒星很难形成。但在观测领域,由于观测信号提取难度大,这一结论一直未被证实。
已有方法行不通,施勇就另辟蹊径,通过研究两个近邻贫金属星系,他发现它们的恒星出生率比类银河系星系的恒星出生率低约10倍到100倍。由此,施勇在国际上首次证实了第一代恒星的低出生率。
顶着39度高烧上山观测
自从与天文结缘,施勇便逐渐养成处变不惊的性格。对天文学家来说,拿到优质的观测数据,“这很需要运气”。
观测的第一步必须要与国际同行“PK”,争取到望远镜观测时间。“观测时间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例如,目前比较昂贵的望远镜——ALMA只向非成员国的科学家开放约10个观测名额,但申请数可能在100个左右,这意味着申请成功率不到10%。”施勇说。
有一次,好不容易等到观测时间,施勇却发烧了。他硬是顶着39度的高烧,开车4小时上山观测,但那次观测的信号太弱,最终失败了。
还有一次,施勇和一位学者赴西班牙观测。两人先后乘坐大巴、缆车、铲雪车,辗转到达观测山山顶。在海拔3000米处,两人都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来不及休息,每晚从12点观测到次日凌晨8点,连续8天、每天持续8小时。
不过,这次艰辛的观测,让施勇在国际上首次在极端贫金属星系中,探测到一氧化碳气体,该成果后来发表在《自然》杂志的子刊上。
“如果想得到重要的成果,就要去寻找别人观测不到的信号,但观测的失败率也很高。不过,我宁可牺牲写论文的时间,也要写观测申请。只有不断参与国际竞争,才能让自己保持对科研的敏感。”今年上半年,施勇一口气又申请了5个望远镜观测时间。
把科幻片当教学片看
每天跟数字、代码打交道,让施勇变得内敛、理性,就连最爱的科幻片和科幻小说,也被他看成了教学片。
“看完电影《流浪地球》后,我回去就开始计算,最后发现,要想把地球推动,真不是几个发动机能搞定的。电影《星际穿越》的场景很震撼,很多画面都是基于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结果,不是虚构出来的。”他说。
施勇的这股认真劲儿,也让他的合作者与学生受益匪浅。他的同事张智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施勇常能基于观测数据,提出多种假设,并提出不同的验证方法”。
施勇的学生李松霖,本科读材料专业,大三时想换到天文专业。“我当时很懵,就给天文系所有老师群发了邮件,想咨询他们需要准备什么。很快,我就收到了施老师的回信,他还把我的邮件转给了相关老师,请他们帮忙。”李松霖说。
凑巧的是,收到回信的第二天,李松霖就遇到了施勇,施勇又给他详细介绍了天文专业,这让李松霖吃了颗定心丸。
此后,李松霖在施勇的指导下完成了天文专业的本科毕业设计,并顺利保送至天文系读研。“很感谢当时施老师为我做的一切,更感谢他告诉我,人还是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李松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