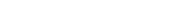我们称为知识或科学的总体概括是一张相互指点、相互教导的思想之网。超文本和电子书写促进了这种互惠作用。网络重新调整了印刷书籍的写作空间,在新的空间,许多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式比油墨印刷更奔放,更复杂。我们可以将生活的整体乐章视为那种“写作空间”的一部分。当气象传感器、人口调查、交通记录器、收银机以及形形色色的电子信息发生器中的数据将它们的“谈话”或陈述大量地注入网络之时,它们就扩展了写作空间。它们的信息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部分,成为我们所谈论的部分,成为我们所意指的部分。

与此同时,网络空间的这种特殊形式也塑造了我们。后现代主义者随着网络空间的形成而崛起绝非巧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统一的大众市场(工业化迅猛发展的后果)已经分崩离析,让位于小型利基的网络(信息化潮起的结果)。这种碎片的集合体是我们现有的唯一完整无缺的方式。商业市场、社会习俗、精神信仰以及种族划分和真理本身的残片分裂为越来越细小的碎片,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这个社会是碎片混战的场所。这几乎就是分布式网络的定义。伯尔特又写?道:“我们的文化本身是一个广阔的写作空间,一个复杂的象征性结构……正如我们的文化由印刷书籍时代进入计算机时代,它也处于由分层次的社会秩序过渡到我们或许可以称为‘网络文化’的社会秩序的最后阶段。”

网络中没有知识的中央管理者,只有独特观点的监护人。人们如今身处高度连接又深度分裂的社会,不可能再依赖中心标准的指导。人们被迫进入现代存在主义的黑暗中,要在互相依赖的碎片的混乱困境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信仰、市场和身份特征。傲慢的中心或潜在着“我是”的工业图标变得空洞乏力。分布式的,无领导的,自然出现的整体性成为社会的理想。
一向富于洞察力的伯尔特写道:“批评者谴责计算机使我们的社会单调同一,通过自动化产生了一致性,但是电子阅读和写作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计算机促进了异质化、个性化和自由意志。

对于计算机的使用后果,没人比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预言错得更离谱了。到目前为止,计算机创造的几乎所有实际的可能性空间都表明,计算机是权威的终结,而非权威的开始。
蜂群的工作模式为我们开启的,不仅是新的写作空间,而且是新的思考空间。如果并行超级计算机和在线计算机网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未来的科技——比如生物工程学——会赋予我们怎样的思考空间?生物工程学可以为我们新的思考空间做的一件事是改变我们的时间尺度。现代人类可以构想十年内的事情。我们的历史向过去延伸五年,我们的未来向前延展五年,不会再进一步了。我们还不具备结构化的方法、一个文化工具,来考虑无论是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的问题。为捉摸基因和进化而准备的工具也许能改变这种状况。有助于利用我们自己心智的药物当然也会改造我们的思考空间。

最后一个难住我们,使我们暂时搁笔的问题是:在网络世界里,思考的可能方式的空间有多大?迄今为止,我们在思考和知识的宝库里发现的所有种类的逻辑,是多还是少?
思考空间也许很辽阔。无论是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个概念、证明一个说法,还是创造一个新的观念,其方法或许都和想法本身一样多。相反,思考空间也许狭小有限,就如古希腊先哲们所认为的那样。我相信,当人工智能真正出现的时候,它会是智慧的,但不会十分类似于人类。它将属于许多非人类思考方式的一种,也许能填充思考空间的宝库。这个空间也将包含我们人类根本无法理解的某些思考类型。但我们仍可拿来一用。非人类的认知方法会为我们提供超越并失去我们控制的美妙结果。

说不定我们会为自己创造出惊喜。我们也许会创造出考夫曼机器似的头脑,可以通过一个小型的指令有限集生成所有的思考类型和所有前所未见的复杂性。也许那可能存在的认知空间就是我们的空间。那么,我们就能够攀缘进入我们所能创造、进化或发现的任何类型的逻辑之中。如果我们能在认知空间内畅行无阻,就能进入无拘无束的思考领域。
我坚信我们会为自己创造出意外惊喜。我也相信,我们的未来是美好!更相信,当人工智能真正出现的时候,它是智慧的。让我们伸出双手,大胆拥抱智慧的世界!